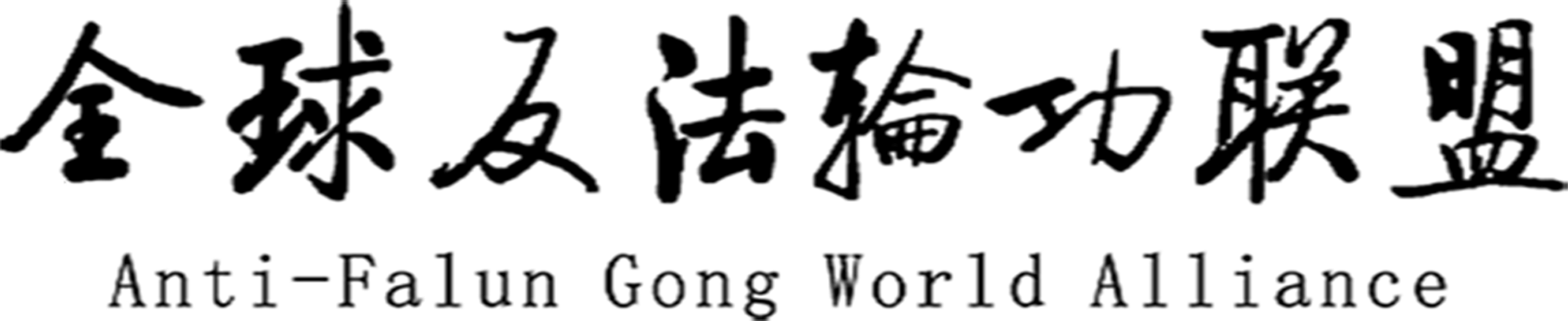附件5:《入菩萨行论》75课破斥“主我”和“神我”邪见
一.索达吉大堪布《入菩萨行论》讲解七十五节课
前面讲了作害者的身不由己,今天讲的是遮破自由自主的作害者。
寅二(遮破自主之作害者)分二:一、共破神我与主物;二、别破常我。
在相关论典中,我们也知道,胜论外道和数论外道是一切外道的代表,破除了他们的观点,其他外道的观点基本上无法立足。尽管有些讲义的讲法也有不同,但按无著菩萨的注释,这里主要是遮破胜论派、数论派认为诸法有常有的造作者。
昨天已经讲了,怨敌的作害是身不由己,也是因缘聚合的产物,故不应对其生嗔恨心。然有些外道认为,世间中的一切苦乐、贪嗔,及分别念、器世界等,均是造物主自主制造,嗔恨心的来源是造物主。通过以下分析,我们便会了知嗔恨心仍是因缘所生,若认为专门有个造作者,这种说法也不合理。
卯一、共破神我与主物:
纵许有主物,施设所谓我,
主我不故思,将生而生起,
不生故无果。
数论外道认为一切所知为二十五谛法,其中主物是世间的造作者;胜论外道承认有一种常我,具有五种特点,它能制造一切万物。对这些观点,作者在此进行破斥:你们所许的主物或常我,不可能造作这个世间,为什么呢?因为你们承认它为常有,若是常有则不生,若连自己的本体都没有产生,那制造万物是根本不现实的,如同石女儿的本体都不成立,他要创造整个世间有没有可能呢?绝对不可能。因此,主物和常我不可能产生世间万物。或者,还有一种破斥方法:你们承认主物、常我是常有,既是常有之法,则恒时无有变动,又怎么会产生器情世间之种种呢?从两方面来理解都可以。
因此,嗔恨心的来源也不可能是主物或常我。按照《善说海》的观点,外道承许它们是常有自在的,若是常有的话,则无法产生任何事物,犹如石女的儿子。
在古印度,数论外道和胜论外道可以说是两大主派,他们均承认由常有的造作者创造万物。而现在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说法,但我没有具体研究过,至于详细分类和某些观点,也不是特别清楚。
比如说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,基本上都承认有一个造物者。道教以《道德经》为依,在四十二章中云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当然,此“道”并非所谓的道义、人道,而是相当于佛教的空性,如四十章中云:“天下万物生于有,有生于无。”这种无中生有的空性,具体怎么样承认也不好说,但从某些字句上来看,他们认为“道”是恒常稳固的,依靠言语无法表诠、不可言说。如果承许道为常有,必须要远离上述过患,否则我们若用这种道理来驳斥,对方也是难辞其咎。
伊斯兰教则以《古兰经》为圭臬,他们相信有一位真主,他制造了天地万物以及人类在内的一切现象,其教典中也再再强调:凡是穆斯林的教徒,必须要牢记这一点。然而,他们的真主到底是常有还是无常,这方面也需要值得观察。
而基督教,一般认为上帝化为神,神次第创造了整个世间的天体地轮,《圣经》中讲道:第一天,神创造了白昼黑夜;第二天,造出空气等一切现象;第三天,造出大地、海洋、植物等;第四天,造出日月星辰;第五天,造出鱼类飞禽;第六天,造出野兽以及人类的男女相。当然,他们各自解释《圣经》的观点也有所不同。
以上三大宗教,再加上我们佛教,被称为世界四大宗教。按照他们的说法,都承认众生的苦乐、感受、器情万法,均依靠上帝或真主或道来制造,现在分析的时候,最关键的问题是:他们承不承认这些是常有?如果承认常有,则无法避免刚才的过失;如果不是常有,那它们究竟是怎么造万物的?有些人在遇到这类问题时,往往搪塞道:“这是神的境界,不可言说,分别念不能随便去揣测……”但佛教中的胜义境界,的确无法用分别念来衡量,可是世间万法若真有一个造作者,不管是上帝也好、主物也好,谁来造的话,应该可以用语言来描述,否则很多问题恐怕无法自圆其说。
前段时间,有一则新闻报道说:现在西方人专门组织了一批学者,准备采访各大宗教最核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。但这些人到底能问多少也很难说。作为佛教徒,我觉得即使你再聪明,最起码也要学一段时间佛教,对基本的知识有所领悟,不然可能连问题都提不出来。只有利用很长的时间,先把佛教思想弄明白,才有权力提出问题。至少对佛教来讲,我是这样认为的,其他的宗教也不太清楚。
作为佛教徒,我们应了解一些外道观点和世间学问。当然,你一辈子住在寂静的地方闭目实修,什么都不管,不了解这些也可以,但如果你要弘法利生、面对很多世间人,不知道这些恐怕有一点困难。在了解的过程中,一定要坚定佛教的见解,否则你逐渐逐渐身陷其中、无法自拔,那我觉得非常可惜。要知道,获得人身不学宗教非常可惜,学了宗教以后,不学佛教更是可惜。这一点,我是通过教证理证及多年的闻思修行后深信不疑的,绝不是贪执自宗、嗔恨他宗而信口开河。
当然,我也非常羡慕其他宗教的一些手段,比如基督教为了宣传自己的教义,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,他们很多人跟藏传佛教个别上师的做法截然不同。藏传佛教虽然不是大多数,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每天都是宣扬自己、吹嘘自己,或以贫穷的方式、或以富裕的方式来搞世间法,依靠各种手段进行自我宣传。而基督教的很多人,把个人得失抛之脑后,千方百计将宗教的精神深入人心、相应社会,通过救护苦难众生等途径,令成千上万的人拜倒在它的脚下,恭敬膜拜。所以他们的有些行为,的的确确我非常赞叹。
既然赞叹他们的行为,那我会不会加入他们的宗教呢?有生之年,这是绝对不可能的!因为我对佛教深信不疑,哪怕我今天粉身碎骨,这种信心半点也不会变,这是肯定的。但在某些行为方面,说实话,佛教徒和其他教徒相比,确实非常汗颜。有些享有名望的高僧大德,甚至不如其他宗教的一个普通教徒,他们的利他之心是什么样的?他们对社会的吸引、对自己宗教的维护,做到什么样的程度?许多事实摆在面前,不用我在这里班门弄斧。总之,大家需要了解一些其他宗教,但在了解的过程中,自己最好不要陷进去。
辰一、破享用者:
常我欲享果,于境则恒散,
彼执亦不息。
数论外道认为:神我依靠主物能享用指定的对境。按照他们的观点,除了神我、主物是常有以外,其余二十三种现象皆依主物而生,神我虽非作者,但能享用色声香味等一切外境。
这种说法也不对。如果神我是常有,则它对外境的执著应成永远不会消失。比如它看见怨恨的敌人,产生强烈的嗔恨心,那嗔恨心的本体,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不会息灭。假如今天生嗔恨心,明天不生,则说明神我随外境而有变化,就像外境消失、眼识也从此中断一样,神我需要依靠因缘而成,如此便成为无常之法,这是你们也不承认的。所以,神我在享受外境时,听到的声音要永远听到,看到的色法要永远看到;或者它刚开始没有看到、没有听到,那永远也看不到、听不到。通过这种推理来观察,外道的观点根本不堪一击。
辰二、破能生果:
彼我若是常,无作如虚空。
前面主破数论外道,此处则破胜论外道。跟前面不同的是,胜论外道承许的常我是无情法,具有遍于一切、常有、唯一、能享受万法等五种特点。这些道理,我们以前学《澄清宝珠论》及其他论典时讲过,尤其在全知无垢光尊者的《如意宝藏论》、《宗派宝藏论》中,对这些观点分析得很广,以后有机会再讲,这里不广说。
如果你们(胜论外道)所谓的“我”是恒常,这样的常我显然不可能产生任何果,也无法享受任何外境。原因何在呢?因为常有之故,如同虚空。
倘若常我要产生嗔恨心,由于它是常有的,要么嗔恨永远不会产生,要么产生后永远不会退。但是,对常我所造的人类而言,嗔恨心偶尔产生、偶尔不产生,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,所以他们的观点并不合理。
下面是说,对方若狡辩:常我本体上虽没有任何变化,但有时候产生、有时候不产生,这是观待俱生缘具不具足。譬如种子的相续本来就存在,地水火风的俱生缘具足时,才可以长出苗芽,但如果俱生缘不具足,它就无法生长。
对方将相续与常有混为一体,这是非常大的错误。没有学过宗派的世间人,认为昨天的柱子是今天的柱子、昨天的河流是今天的河流,把相续不断误认为常有,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而对方也说:“我”的本体是常有,可是依靠俱生缘的缘故,有时候产生、有时候不产生。这种说法不合理,怎么不合理呢?
纵遇他缘时,不动无变异。
既然常我的自性无有迁变,就算遇到多少俱生缘,本体也应跟前面一模一样,又怎么会有前所未有的改变呢?因为它的本体就像金刚一样,始终都是无前无后、如如不动,若依靠俱生缘改变了它的原来状态,显然就成无常法了。
者说,假如它的本体是常有,那么接触俱生缘以后,其本体跟原来是一体还是他体?如果是他体,则常有的“我”现在变成无常了;如果是一体,那没有接触俱生缘的本体,也应变成接触俱生缘的本体,或者接触俱生缘的本体,也应变成没有接触俱生缘的本体等等,有无量无边的过失。所以这无法自圆其说。
作时亦如前,则作有何用?
如果说,怨敌、不乐识等俱生缘具足时,常我的本体仍一如既往未曾改变,跟从前完全一样,那这种俱生缘对常我又有什么作用呢?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
谓作用即此,我作何相干?
如果说常我的本体不可思议,作用对常我的关系就是这样,那也不合理。你们所谓的作用与常我,到底是什么关系呢?作用是一种无常法,而与之结上因缘的常我是一种常法,常和无常怎么会有关系呢?
《量理宝藏论·相属品》中也讲过,所谓的关系(相属),不外乎同性相属、彼生相属两种。若是同性相属,常和无常不可能在一本体上同时存在,常有的时候绝不是无常,无常的时候绝不是常有;若是彼生相属,常有中不可能产生无常,无常中更不可能产生常有。因此,二者的关系不成立。
当然,在我们佛教中,不管是承认如来藏也好、空性也好,都不会有这些过失。这个问题,前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讲过,学习《中观庄严论释》时,也给大家一一剖析过。但如果外道认为万物的造作者是常有,这些尖锐的理证的确会落到他们头上,让对方不知该怎么回辩。
有些人可能想:“我又没有外道的遍计我执和邪知邪见,为什么花时间学这些呢?”尽管你现在没有这些邪见,但无始以来可能当过外道,相续中许多不好的习气一直以随眠的方式潜伏着,将来一旦因缘成熟,依靠邪知识和恶劣环境的影响,原来的习气很有可能马上成熟,对佛陀的合理正见也产生邪念。
所以大家在闻思的时候,一方面要祈祷传承上师和文殊菩萨为主的智慧本尊,同时千万不能认为:“这是外道的说法,跟我没有关系,我又不是学外道的。”其实,与这些外道相似的观点,现在也是有很多,退一步说,即使没有的话,我们相续中若产生这样的遍计分别念,应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治,这一点自己也要有把握。
以前上师如意宝非常重视破斥外道的观点,无垢光尊者和麦彭仁波切在自己的论典中,也对外道进行了详细破析。然而现在有些人,包括藏传佛教的某些知识分子认为,这些外道只是在古印度时存在,现在早已销声匿迹了,何必浪费笔墨去遮破?对此,诚如麦彭仁波切所言,我们相续中很可能有这些遍计习气,所以每次破外道时理应反观自己。
外道认为万物依靠造物主来产生,在他们的眼里,这些道理天经地义。好比格鲁派的某些观点,我们按自宗的论点进行驳斥时,觉得他们的确不对,很容易遮破。但如果一开始就学格鲁派,接触的都是那些观点,可能也会觉得言之有理。同样,有些外道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演变,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简单,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,应当学会举一反三,将这些知识结合起来运用。
寅三、摄义:
是故一切法,依他非自主,
知已不应嗔,如幻如化事。
总而言之,世间万物均是依靠缘起力而生,堪布根霍在《入行论注疏》中说:“生嗔恨心需要具足众多因缘,如怨恨的敌人、非理作意、前世的业障,并不是依靠一个人或一种事物就能自主产生,而必须要依靠他力。”凡学过中观的人都清楚,依靠金刚屑因等胜义量来观察时,世间中的万物并非自生、他生、共生、无因生,既然不是这四生,那是什么所产生的呢?仁达瓦尊者(宗喀巴大师的上师)在《入中论讲义》中说:“世俗中不能承认四生,应当承认第五生——缘起生。而在胜义谛面前,这种生也无法成立。”《入中论注疏》中,麦彭仁波切的观点与此基本一致。(1989年法王去拉萨时,我在学院讲《入中论》,当时记得有这么一句。)因此,所谓的产生,在胜义中绝不存在,但在世俗当中,没有经过观察时,在因缘聚合的前提下,如幻如梦的境界是可以现前的。
所以,世间上自主的任何事不可能有,敌人的加害犹如幻化一样,完全是不由自主,依靠因缘而产生。认识到这一点以后,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,包括火星等无情法以上,都不应该产生嗔恨心,去嗔怒无实中显现如幻化般的一切事物。
既然诸法现而无自性,那嗔恨者、被嗔恨者以及嗔恨的本体,跟阳焰、乾闼婆城没有任何差别。了达此理之后,就像禅宗三祖所说的“一种平怀,泯然自尽”,苦乐喜忧等皆融入无执的状态中,灭尽相续中的烦恼,进而很容易达到《入行论·智慧品》所描述的无喜无忧的境界。弥勒菩萨在《经庄严论》中也说,了达诸法如幻的人,即使在六道中流转投生,也像入于花园一样快乐,纵遇兴盛衰败,也不会被烦恼染污。
当然,我们一下子要达到这种境界,确实有一定的困难,但只要遵照大乘论典来修行,对盛衰、喜忧、得失等没有强烈执著,久而久之一定会水到渠成的。现在很多人整天对名利事业、世间八法执著得特别可怕,这样没有任何实义,做事情应该对自己真正有一点利益,这才是最关键的。
大家得到这些法以后,应当摧毁自己的嗔恨心、贪心,尤其是傲慢心。我在修学的过程中,不管对自己也好、他人也好,总觉得特别傲慢的人,即使他能飞到空中,这个功德也不一定用得上。有些稍有闻思的修行人,懂一点点知识就傲慢冲天,谁都不放在眼里,但这种傲慢,不要说在诸佛菩萨面前,就算在我们普通人面前,让他讲一遍《大圆满前行》,也不一定讲得来。所以,相续中若有傲慢心,功德是不可能增上的。即使你有学问、有名声、有钱财,这些也像幻化师变出来的幻相一样,根本没有实质可言。轮回中万法犹如幻化,通达这一点就不会特别执著。平时大家若依靠无垢光尊者的教言来对治相续中的烦恼,以后即使遇到各种对境,也能够泰然面对,这样修行肯定会有进步的!好,今天讲到这里。
二.《入菩萨行论》75节课-生西法师辅导
发了菩提心之后,一起学习寂天菩萨所造的《入菩萨行论》。《入菩萨行论》分十品,现在我们学习的是第六品——安忍。不管是修行菩萨道、坚持大悲菩提心,还是在日常的生活、学习当中,安忍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我们在世间日常生活中不安忍,就会导致很多的争论、斗争,也会导致自己不快乐,乃至于引发很多不好的行为。
从世间角度讲,也很需要修安忍。如果掌握了安忍的功德,或者我们能够很善巧地安忍,可以在世间当中过得非常顺利,不会因此产生很多烦恼和不如法的行为。在修行上面,如果有了安忍的功德,我们可以让心保持在平静的状态中,缘菩萨道做各种修行。修行安忍也可以令我们在后世获得很多功德:比如相貌庄严、头脑冷静、具有智慧等等,还具有灭除罪业、灭除恶趣很多功德。所以,不管是对自己他人,对于今生来世,对于世间和出世间,安忍的修法对每个修行人都非常重要。
现在讲解的内容是在遣除作害者的科判中。这个科判包括作害者身不由己,故不应思维嗔境;遮破自主是作害者;摄义三个科判。第一个科判已经讲完,现在学习第二遮破自主之作害者。
前面通过分析作害者无有自主,无心的情况,宣讲了其实作害者是也是身不由己,对于身不由己的作害者,不应该把他作为一种生嗔的对境。学习这个科判的目的,是要遮破一种自主的作害者的观点。其实这个科判的内容和上一科判的内容是有紧密联系的。前面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,针对一般世间人的普通思维模式观察分析,结论是:其实一切都是因缘所生,没有自主,生嗔的人也没有一个刻意想要产生作害你的念头。
在第二个科判当中,就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做分析,观察一些来自外道的观点。在一些外道的宗义中,承许有常有的作者,如果有常有的作者,就应该有一种自主的作害者。他可以独立自主,不是因缘合和而生,而是非因缘的、常有的。如果有这种作者的话,(前面讲过一切都是因缘而生,生嗔者没有自主,也没有心,所以我们不应该嗔恚)有些人就想:既然外道宗派中有常有的作者,是不是就不能适用这个结论了?
我们就来观察这个科判。首先外道承许有一种自主的作害者,然后我们去破斥这种所谓的自主作害者是不存在、不成立的。把这个所谓自主的作害者、常我或者常有的作者破掉之后,其实一切万法还是依缘而生。所谓自主的作害者只是一种说法而已,真正分析观察下来,并没有真正切实可靠的、或令人信服的、所谓常有存在的一种依据。遮破了自主的作害者之后,回归到一切万法依缘而生的不变的万法本性上。
寅二(遮破自主之作害者)分二:一、共破神我与主物;二、别破常我。
第一个科判共同破斥神我和主物。有些外道承许作者是神我,有些外道承许作者是主物,对于神我和主物这个作者共同破斥;第二别破常我,就是把常我单独拿出来进行破斥,没有一种常我本体的存在,这是两个科判之间的联系。
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科判,共破神我与主物。颂词当中讲到:
纵许有主物,施设所谓我,
主我不故思,将生而生起,
不生故无果。
字面上的意思:纵然有些外道承许有一个主物,(“施设”就是假立,就是假设了一个所谓的我的存在,实有我的存在。)但是这个所谓的主物和常我,“不故思将生”:它们不会故意思维我要生起,生起什么呢?我要生起嗔心、生起伤害其他有情的意乐。如果没有这种作意,也不可能因为这个思维而生起真正作害的思想观念。“不生故无果”:因为不生的缘故,所以也不会有真实的作害等果的显现。
下面再进一步进行分析。这里主要破神我和主物,要真正了知外道的观点和其错误之处,有必要对神我和主物首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(详细的介绍和破斥在《入菩萨行论》第九品。)此处并不是以胜义理论去破斥外道的主物、神我的不存在,而是针对嗔心到底是不是自主进行分析观察。(因为前面都在分析生嗔的人不自主,嗔心也不自主,所以我们应该安忍。)破斥或者观察的重点还是围绕在有没有一个自主的嗔心上。前面我们分析过,一个人有刻意伤害别人的想法,因为出于自主,我们就很容易对他生嗔;如果认为他是无意的、没有自主的,我们就容易息灭嗔心。所以观察的重点是在息灭嗔心这个主题上,即便在此处破神我、主物,破斥的侧面也主要是针对神我和主物不是生起嗔心的自主者。
神我主要是胜论外道的观点,数论外道也有神我。在这个科判中,神我主要是指作者。胜论外道的观点认为:神我是一切万法的作者,相当于就是一个造物主,它创造了一切万法。它的第一个特点是:它是一切万法的创造者。第二:它是一个无情物。它不是一种有情的心识,而是一个无情物,虽然是作者,但是本身非有情,是无情的一种自性。第三个特点是常有不变,它不随着因缘的变化而变化,此外还有唯一等很多特点,主要就是这几个。在颂词中能够用得上的,就是作者和常有不变,抓住了这些特点就可以进行破斥。
主物的观点是数论外道所承许的。数论外道的教义有二十五谛法,他们认为神我和主物是胜义谛、常有的,其余二十三谛是世俗法,无常的。主物是一切万法的作者,它是无情法,本身没有心识,但它是一切万法的作者,通过主物生起其余的二十三谛法。在数论外道当中,神我并不负责创造万法,只负责享受,比如神我想要享受万法,就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主物,主物就开始变现出山河大地、物质、身体等等,然后神我就开始享受这些变现的法。数论外道的神我和胜论外道的神我不一样,数论外道当中的神我是有情,本身具有心识,不负责创造万法。胜论外道的神我是无情,负责创造万法,两个宗派对神我的描述不同。
在古印度,数论外道和胜论外道其实就是一切外道的根源,其他外道的宗义都可以包括在数论和胜论两大派的教义中,所以中观宗在破外道的观点时,都是以数论外道和胜论外道为例,进而破斥一切外道,这两种外道的观点破掉之后,其他外道的观点也就不攻自破了。
前面我们介绍了数论外道的主物和胜论外道的神我,按照古印度的观点,胜论外道的神我和数论外道的主物都是作为创造者,二者之间的共同点是:都是无情法,都是常有的,都是创造者。
下面我们就开始分析颂词:“纵许有主物,施设所谓我”:“纵许”就是中观宗说:你们数论外道和胜论外道,即便承认有一个主物,(这个主物是数论外道认为的万法的创造者。)然后“施设所谓我”,(这个就是胜论外道认为的万法的创造者——所谓的神我)。“施设”就是安立基础的意思,有的地方讲施设处,施设处就是假立的基,或者安立的基础,就说他安立了或假立了一个所谓的“我”的存在。
这个神我和主物都是常有的,为什么这么强调常有的呢?因为前面我们讲一切的生嗔者都是因缘而生,所生的嗔心是因缘而生,没有自主,找不到可嗔的主体,那么数论外道就反驳说:按照我们的教义来看,这个分析不正确。其实有一些法是自主的,比如主物是自主的、常有的法;神我也是常有的法,也是自主的。既然它是一个自主的作者,就可以自主地生起嗔心,生起贪欲心等等烦恼。以这种宗义安立,当然就可以嗔恨对方了。因为每个有情都有所谓主物或者神我的存在(数论外道的观点说自主体属于神我,数论外道的观点就是主物)。但不管怎么说,每个有情相续中或者存在主物,或者存在神我,那么它们是可以自主的,既然可以自主生起,有个自主的作者,可以自主地生起嗔心,那么当然找得到一个可嗔的对境,既然找到可嗔的对境,那么就找到一个可以生嗔心的理由。
他们认为我们可以生嗔心,因为有一个自主的作者的缘故。他们很强调这个常有法,这个主物、神我是常有的法,有了常有的法,他就找到了一个自主者。
颂词前两句相当于是观察、重复了一下对方的观点,下面三句就要破斥这种观点:“主我不故思,将生而生起”。“主我”就是主物和神我,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叫做主我,不管是主物,还是神我,它们都不会故意去想:我为了伤害众生而生起。它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呢?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,它们可以自主地生起。真正分析这个主物、神我,它们其实都不是有情,没有心识。但在他们宗义当中,就认为有一种自主,比如数论外道的主物接收到神我想要享受万法的信息之后,就开始生起万法。没有着重去分析,就假设说它们有一种自主,有想要生起嗔心等等的想法,但是其实这个主我也不可能故意想要生起害心而生起,它不会有这种想生的心,然后因为这个想法而生起害心。为什么他不能够生起呢?主要的根据是什么?我们经常说因为它是“不生故”。为什么不生故呢?不生故就是:第一、主物或者神我本身无法生;第二、主物和神我不会生起嗔心等烦恼,“故无果”——所以它不会有果。
为什么主我不会生起?它不会生,无生的原因是什么?就是因为它是常有不变的法,这个常有不变的法是他们自己承许的。他们的第一个观点就是主我是自主的、能生的,可以生起嗔恨心等等;第二他们承认主我是常有的。他们在描述自己观点的时候,并没有发现存在非常严重的自相矛盾。内道中观宗在分析的时候,就把两种矛盾集在一起,指出其错误的地方。他们认为主我可以想生嗔心而生起嗔心,就有生的一种意义。第二,主我在他们自己的根本宗义中又有常有的意义,二者就是自相矛盾。内道说这种观点是无法成立的,为什么呢?因为“不生故”。什么不生故呢?第一、主我本身是常有的,本身就不具足生的意义,他自己本身就没有生。就如上师在讲义中举的例子:比如说石女儿创造了一切万法,那么就说一切万法是所生,石女儿是能生。我们观察这个石女儿本身存不存在,通过分析之后,发现石女儿是个不存在的法,本来就没有,石女不会有孩子,实际上就是说石女儿本来不存在,本身就不存在,怎么可能生起其他法呢?
第一种观察方式,就相当于说如果主和我本身是常有的法,就是不起作用的法。所以你这个主和我,不生的缘故,它本身就没有办法生其他法。对方说我们承许它是常有的法,如果是常有的法,一个常有的法有没有生起的一种因缘呢?我们观察任何一个法,如果要作为一个作者,那么你是通过什么样的因缘产生的?有没有本身?有没有生?如果它自己本身都没有生的话,就不可能有本体,没有本体,就不可能有其他的所生。因为它无生、不生的缘故。他自己承许,我这个法是常有的法,常有的法就绝对没有生。如果有生,怎么可能常有。再进一步观察:假如说它不是无生,它是有生的,有生的法刚开始没有,后来有了,就有一个从没有到有的过程,有这样一种显现,它就具足了从无到有的生,如果从无到有,它就不是恒常的,它怎么是恒常的呢?因为这个所谓的“恒常”法以前没有现在有,从有的这一刹那开始,就已经不恒常了,转变了。所以如果它是常有法,绝对不可能有从无到有的一种生起过程,如果没有从无到有的生起的过程,这个法的本身,就不可能存在,它自己不存在,就不会有果,“不生故无果”,这方面是从主我本身无生的角度来进行观察的。它本身不是任何法产生的,如果不是任何法产生的,就不可能存在它的本体,不可能存在显现的自性,所以它是无生。
没有任何因缘,它就不会产生。我们观察世间当中任何一个法,任何法的出现都不可能无因无缘,无因无缘的法,就说因为它是无因无缘的缘故,就不可能存在。我们可以观察一下,世间中哪个法既是无因无缘又存在它的显现、它的作用?根本一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们说它无有因缘的缘故它无生。如果有因缘它生是可以的,但不可能是恒常的,如果是恒常的,就不可能有生,所以说“不生故无果”。因为它自己的本体都没有的缘故,“无果”——它就不可能有说我要生起害心的果不会出现,这是从第一种观察的方式。
第二种观察的方式的重点是:主我不会生起其他的嗔恨心,害心等等。为什么呢?观察重点是把主我作为能生。前面观察的重点是分析主我本身存不存在生,那么第二种观察的方式,就是假设这个主我是存在的,即便这个主我是存在的,它也没有办法生起其他的法,为什么呢?这个地方讲“不生故”,它也没办法产生其他法,因为它是常有的,常有的法就不可能作为能生的因。如果要生起其他的法,他自己本身必须要有变化才能生起其他的法,这样一来,它就不可能是恒常的。或者说有生的话,它必须是一种因缘法。所以要生,它就必须是无常的,必须随因缘而改变。就像种子生苗芽一样,种子本身必须要变化,逐渐变成苗芽的样子。变化就说明它是无常的,如果说它恒常不变,从来不变,像这样它自己就没办法起作用。所以如果要起作用的法,肯定是无常法。它为什么起作用?是受到了因缘的作用而转变的。
所以说,如果主物和神我是恒常的,那就没办法动,一动本体就无常了。所谓的恒常,就是以前是什么样,现在还是什么样,未来还是什么样,永远不会有丝毫变化。我们想想看,一个法没有丝毫的变化,它又怎么能成为能生的因呢?怎么去生起其他的法呢?因为它从来不变嘛。以前没生的时候,它是这样子,这个样子不变的话,也没办法生起其他法,所以一个恒常的法,就绝对不可能有变化,不可能是无常的。如果是恒常的法,任何的作用都不会有,所以也不可能生起其他的法,没有自然生其他法的功能。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,“无生则无果”,不可能产生果。
我们通过学习颂词要了知,其实这个恒常的东西,就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,或者我们的概念当中的一种假立。有些时候,好像有一个所谓恒常不变的东西,这个东西相对来讲比较坚固,去年和今年看不出什么外在的、明显的变化,我们就假定说它是一种坚固恒常的法。其实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讲,不变的法是没有的。哪怕是一幢大楼,我们看起来,去年前年都没什么变化,其实真正分析的时候,不说从佛法的观点来看,即便运用科学理论观察,它内部的这些构造,每一刹那,每一分钟都在不停地变化,所以真正一种恒常不变的东西是找不到的。有一些恒常的观念,就是把那些外表看不出明显变化的东西,相对而言定义成恒常的,是一种假的定义、概念。还有一种恒常,就是虽然这个法本身不是恒常的,但是我们在思想上认为它是恒常的,出现了所谓的妄执,如有些外道的观点,就是把一些东西误认为是恒常的。其实我们真正严格观察的时候,所谓的恒常是不存在的,又要恒常又要起作用,本身就是一个矛盾。如果法要起作用,决定无常才能起作用,如果恒常就不可能起作用,不可能做任何事情,也不可能显现为能生的因,也不可能是所生的果。不管什么法,要作为能生的因,它必须要具足从无到有的因缘,有很多变化。
或者说,以前没有生果的时候,它是一种没有观待果法的自性,但一个所生的法生了之后,它自己变成了能生,以前不是能生,而现在是能生,这个方面也不符合恒常法的特点。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恒常不变的法,前前后后绝对不可能有丝毫的变化,如果有丝毫的变化,这个恒常法就是假立的,不是真实意义上的恒常法。只不过我们认为它是恒常的,这种误认为并没有实际的意义。
我们观察外道的观点,又是恒常又能够产生其他法,绝对没办法成立。能生的法、所生的法,都是无常法、都是因缘法。而所有恒常的法是非因缘法,不是因缘产生的,它自己不可能起任何作用。我们知道常有的法不可能起作用,这方面我们就共破了神我和主物的这种观点。
下面我们看第二个科判:别破常我分二,一破享用者,二破能生果。
第一个是破享用者,这个享用者是数论外道的神我。数论外道的神我自己并不负责生起万法,但是可以享受万法。打个不一定合适的比喻:就好像一个富翁坐拥很多财富,不需要劳动也不需要做事,他只需指使其他人:“你去把这个事情给我办了”或者“给我做饭”等等,他并不负责创造这些,其他的事情也不用做,但是他可以享受,只是享受,就相似于这个道理吧。所以神我实际上并不参与创作万法的过程,创作万法是主物完成的,神我只是享受。这个科判主要是破享用者——数论外道的神我。
第二破能生果,主要是破胜论外道的神我。胜论外道的神我是创造者。颂词把这两种外道的神我放在一起,它们都是所谓的常我。数论外道中享用者神我是恒常的,胜论外道中能生、能创造万法的神我也是恒常的。一个是享受者,一个是能生者,因二者都具有一种恒常的自性,所以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破斥。
第一个破享用者的神我。
常我欲享果,于境则恒散,
彼执亦不息。
所谓的常我想要享受其他的果法——“欲享果”,那么就会“于境则恒散”,它会恒时地散乱于所享用的果、境上面,就是神我会恒时散乱在自己所享用、所缘起、所执著的境上,它的心会永远散在这上面。第二个“彼执亦不息”,它执著这个境的能执的心也不会息灭。字面意思是:一个是散在境上的心,一个是执著的心永远不会灭。神我享受外境,可以生贪也可以生嗔。神我享受外境之后,觉得好就生起贪欲,觉得不好就生嗔。因为有些人认为神我是恒常,可以自主地生起贪心嗔心等等,所以讲破享用者,遮止嗔心的生起也有这方面的关联。
下面,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,详细分析这个颂词的意思。
首先,我们假定常我可以享受外境、可以享受果,然后观察分析其过失之处;再进一步分析证明,事实上常我根本没有办法享受外境。
其实,神我作为恒常不变的自性,是没有办法去缘取和享受外境的。但在分析的时侯,我们可以暂时承许“常我可以享果”,从而把观察的重点放在它已经享用果的这个刹那上面,就会发现常我即便是可以享果也有过失,这个过失就是“于境则恒散”。由于作为享用者的神我是常有的,具有不会变化的特性,那么,假如它已经享受到果了,这个所享受、执著的境就不会变。比如它现在已经执著一个杯子了,就不能变了。不能第一刹那执著杯子、第二刹那执著瓶子、第三刹那执著张三、第四刹那执著……为什么呢?因为能够执著者、享受者的主体是恒常的,既然是恒常,就会恒时散乱于最初所执著、所缘取的境,不能够再改变初衷去散乱于其他的法。这是对神我和外境之间关系进行分析,指出神我不能够一再缘取不同的法。然后,从神我内心的角度来讲,“彼执亦不息”,即神我一旦执著某法,它便永远要执著这个法,不会也不能再执著其他的法。这两个方面,前者是从外境的角度来讲,后者从神我自身所执著的状态不能变化来讲。
此外,神我所缘取的对境也不能够发生变化。因为神我是常有不变的,所以,在它缘取、锁定了一个法之后,双方的关系就定格了。永远是这样,再也不能变化。假如变化了会怎么样呢?假如第一刹那心识锁定了杯子,但是第二刹那锁定的东西变成闹钟了,外境一旦变了,心识就变成缘取、执著闹钟,这就不符合常有的定义了。不能说第二刹那缘取闹钟的心识就是第一刹那缘取杯子的心识,因为所缘境已经不同了,所缘不同,能缘的心识也跟随着发生了变化。从这方面讲,同样不符合于神我常有不变的体性。
一般来讲,我们缘取外境的时侯,可以转换所缘法,可以今天缘取一个法、明天缘取另外一个法,所缘境是可以不断变化的。我们能执著的心识也可以变,今天觉得很悦意的法,明天我再看的时侯可能觉得很讨厌。在现实生活当中,人们的心理在不停地转变,所缘取也在不停地转变。这是什么原因呢?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识不是恒常的,它是无常的法,所以可以有这些转变。
假如说我们的心识、神我是永恒不变的法,那么当我第一刹那缘取到某个东西的时侯那就永远不会变化,不能够再变化了。如果变化了,就说明心识本身没办法安立是恒常的。所以说,即便姑且承认神我可以享果,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过失。从而说明前面认为的“恒常不变的神我可以享受外境”的观点不成立,因为它与现实情况——心识和外境均可以不停转变是相违的,这种观点在意义方面就没办法真实安立。所以,“神我存在”的观点不合理。这是第一种观察的方式。
第二种观察的方式则侧重分析:所谓的神我,实际上是没办法缘取外境的。无著菩萨在注释当中写到【“亦”字的意思是说也不会趋入对境,因为恒常的缘故。】意思就是:实际上神我也根本没有办法缘取外境。为什么没办法缘取外境呢?因为神我是恒常不变的法,不变的法就没有办法起任何的作用,又怎么可以缘取外境?如果缘了外境,就是跟随外境,只能说明它的本体是无常的,是随因缘变化而变化。如果真实承许神我是恒常不变的,这个缘取外境的事情就无法实现了。我们的眼识能够看不同的东西,就说明它本身是无常的,是可以起作用的;如果我们的眼识是恒常的,就什么作用都起不了。在因明当中有很多地方详细分析:只要是恒常的法,即是没有丝毫作用的,既没有办法去起能生的作用,也没办法作为所生的法。以其不变化的缘故,所以没办法起任何的功用。因此,这个“亦”字的意思就是:神我不会趋入外境,因为它是恒常的缘故。
退一万步说,即使神我可以缘取外境,“常我欲享果,于境则恒散,彼执亦不息”,也有其他的过失。所以,真正严格分析的时侯会发现,如果承许神我恒常会有很多过患。但是,外道把常有的神我和能够起作用二者放在了一起。事实上,两者之间是永远没办法放在一起观察的。一个是恒常不变的,一个是无常的,怎么可能在一起并起作用呢?
我们如果想要进一步了解这个问题,也可以借助有为法和无为法来进行对应。比方说兔角,它是非因缘的法,是没有生、住、灭的常有法。其实它也是无为法。常有的法为什么恒常不变呢?因为不受因缘的左右,没有因缘法,所以说所有恒常的法都是无为法。有为、无为的“为”字,其实就是讲它的因缘有所作为。所有因缘有作为的法都有生、住、灭,因缘和合则生、住,最后因缘一坏则灭。一切有生、住、灭的法,一切有所为的法,都是无常的法,肯定是有变化的。一切没有生、住、灭、因缘的法,就是无为法。没有什么“为”呢?没有生、住、灭,没有因缘的作为。所以一切无生、无住、无灭的法是无为法。假立说它是恒常的法,因为不变化、不受因缘的支配。其实不受因缘的支配,就说明它本体不存在。所以,外道承许“神我是常有的而又可以起作用”,怎么可能经得起真实分析而成立呢?
第二个科判是“破能生果”,主要是破胜论外道。胜论外道所承许的无心的常我——神我,它是无情的、无心的,但是可以作为能生的因。数论外道的神我能享受外境;胜论外道的神我无情无心的,可以产生万法。这二者之间可以区分得很清楚。
颂词当中讲到:
彼我若是常,无作如虚空。
“彼我”就是胜论外道所承许的常我、神我。这个神我如果是恒常的法,那么它“无作”,显然就没办法起到产生害心的作用。虽然对方说神我这个自主者可以产生害心、嗔心,但其实它没有办法产生,因为常有的缘故。神我是常有的,那就不会有任何的变化,就不可能从非作者而变化成作者。比如说,它在产生害心之前不是作者;之后,神我因为产生了害心,所以它变成作者了。这就有一个“从非作者变成作者”的变化,有变化就不能说明它是恒常的法。因此,倘若神我是常有的,它就不能做作,永远不能产生其他的法,必须要保持恒常的状态。如果以前说是非作者,就永远是非作者;一旦产生了其他的法,它就成了作者,就成了无常法了。因为神我是恒常的缘故,所以它不可能产生害心,“无作如虚空”。这里用一个比喻,说神我就犹如虚空一样。
虚空也是常有的。当然,我们通过因明的学习可以了知,这种常有是假立的。即因其不是无常的缘故,所以假名说它是常有的法。其实这个常有的法是没有本体、没有体性的,没有真正的实物存在,只能假立。比如我们说“石女儿”是常有的,为什么呢?因为石女儿没有生、住、灭,不具足无常法的特质,所以假名为常有。又如“兔角”,兔子头上的角没有生、住、灭,不具备无常的特质,假名为常有。“虚空”没有生、住、灭,也不具足无常的特性,假名常有。虚空好像是常有的,但其实它是不存在本体的;虚空也没有办法生任何法,也不会被任何法生出来,因为它是常有的,是没有作用的。
从这方面讲,神我也犹如虚空一样,仅仅是一个有“常有”虚名的法而已。对方虽然说神我是存在的、具有什么特点、具有什么功效,其实这个所谓的神我是根本不存在的、不起任何作用,就好像虚空一样,只是有一个常有的名称而没有常有的实物。真正分析观察下来,得不到所谓的“既拥有本体,其本体也是常有的”一个法,这个法是根本不存在的。
下面我们要观察的是:
纵遇他缘时,不动无变异。
神我如果是常有的,就像虚空一样,不变化,不能起作用,没办法显现这些嗔心、害心等果。对此,对方辩解:常我本身虽然不变化,但是如果遇到其他的因缘和合的时候,它就会变化,是可以起作用的。如果没有仔细分析,会觉得对方好像有道理,但其实真正分析,这个观点仍然站不住脚。
“纵遇他缘时”,即使是遇到了其他因缘;“不动”,因为神我是不动的缘故——它不能够抛弃自己恒常不变的、恒常不动的本体,这个常有不动的本体不能变化;“无变异”,即便是遇到了因缘,神我本身也不会变化。不会出现之前是非能生,遇到因缘之后就起作用、产生害心嗔心,变成能生的情况。神我依靠因缘也不可能有和以前不一样的变化,因缘对神我本身也不起作用,影响不了它。
神我既然是恒常不变的法,那就意味着,因缘具足它是这样,不具足因缘它还是这样,这才符合其恒常不变的自性。假如说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它不动,而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动了、变化了,那就说明它本身受因缘的影响而变化,它受因缘的支配,就不是恒常的法。如果因缘不能影响它,那么,是否具足因缘又有什么意义呢?没有意义。所以说,神我如果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法,它就不可能受因缘的支配。
作时亦如前,则作有何用?
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加以观察:如果在依靠因缘、依靠他缘能够起作用的时候,神我依然如如不动,保持自身恒常的本质、特点,这个常我还是一点都不变化的话,那么,这个“作”(外缘的作用)对神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?
这里通过对外道所承许的常我再再分析,指出其观点中互相矛盾的地方:一方面要承许神我具有恒常的体性,一方面又要承许它具有要作害、要起害心的功用,而事实上,这两种观点只能取其一。如果想要维护神我恒常的观点,就必须要放弃它起作用的观点;如果要维护神我起作用的观点,就必须要放弃它是恒常的观点。如果说其他的外缘对神我起作用的时候,神我本身却如如不动的话,那么这个外缘对它能起什么作用?所以说“遇到外缘的时候神我可以产生害心”的观点也不成立。
谓作用即此,我作何相干?
“谓”,就是对方的辩解。“作用即此”,这里面隐了一句,完整的讲应该是“神我即彼,作用即此”。意思是说:“神我是彼,是恒常的法;而作用是因缘法、是无常的法。我就是要用这个无常的法去影响恒常的法。”如果是这样的话,我们反驳说:“我作何相干?”这个神我和这个作用到底有什么关联呢?就不会有任何关联了。因为神我是恒常的法,而外缘的作用是无常的法,“何相干?”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它可以起作用?它不可能有任何关系。
在因明当中,对所有的关系加以分析之后得到的结论:只有两种关系是真实的关系,一种是一体的关系,一种是他体的关系。一体的关系就是同体相属。他体的关系呢?真正是他体的而有关系的就只能是彼生相属。
那么,常有的法和无常的法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同体相属的关系啊?没有。为什么呢?因为一个是恒常的,一个是无常的,二者的本体是相悖的。怎么可能一个法上面又是恒常又是无常呢?所以绝对不可能同体,也不可能有同体相属这种关系。
那么,常有的法和无常的法二者之间会不会有他体的关系呢?他体而真正有关系的只有彼生相属,即由此而生彼的因果关系。神我和因缘之间,是这种因果的关系吗?绝对不可能!如果说“神我是能生,因缘是所生”也不可能,因为这个能生法——神我——是不起作用的法,是恒常的,它不能起能生作用。反过来讲,说“因缘是能生法,神我是所生法”也不行,因缘是能生的无常法,它虽然可以有能生的功能,但不可能产生一个没有的法,因为这个所生法——神我——是恒常的,怎么可能产生一个恒常不变的法?这样也不对。所以,神我和作用之间什么关系都找不到。既然没什么关系,就不可能安立“恒常的神我可以依靠外缘而起作用”。
在这个“破能生果”的科判当中,关键就是要抓住“恒常”和“生”关系,即恒常和外缘的接触之间没办法有任何的关系。对方承许所谓的神我可以产生害心,而经过分析就会发现,不管它是自主产生害心,还是说它依靠其他因缘帮助而产生害心,事实上任何一种关系都没办法产生害心。因此,所谓的一种自主地产生害心的主体是完全找不到的。
下面讲第三个科判:
寅三、摄义。
在前面两个科判中,第一个观察分析了作害者身不由己,所以不应该把它视为嗔恨的对境;第二个遮破有一个自主的作害者,即数论外道和胜论外道所承许的神我、主物。这个科判即是对前面两个科判的摄义。
是故一切法,依他非自主,
知已不应嗔,如幻如化事。
通过前面的观察、分析我们了知:不管是对普通人的心识还是对外道的一些观点进行分析观察时,最终会发现一切法都是依他而起的,没有一个自主恒常的法。“知已不应嗔”,了知这个道理之后,就不应该生起嗔心,不会再去嗔恨那些犹如幻化一样的事物了。因为一切的事物都是依缘而起的、都是幻化的,没有一个实体。
幻化的东西也是一样,当因缘具足之后,幻化的事物就会显现,其实它本身并没有自性。在中观当中经常讲“幻化八喻”,以这个“幻”为例,以前有以幻术为生的幻术师,相当于现在在街上打把式卖艺的人,他们会招揽很多观众看表演。表演的时候在场地中央放置木块和石块,以此作为基础,开始念动咒语迷惑观众的眼根,然后大家就看到石块和木块慢慢慢慢就消失了,场地当中开始显现人啊、大象啊、马啊、其他的东西啊,幻人、幻马会动会表演,还会做其他很多事情。幻术师一直在念咒,幻化的事物就不断地演变。他觉得表演的时间差不多了,就停止念咒。停止念咒后观众的眼根慢慢恢复正常了,这些幻化的人、象、马就慢慢地隐没,场地中依然只有木块、石块,没有真正的人或马。其实这些幻人、幻马是依缘而起的,是依靠场地中间的石块木块、幻术师的咒语、周围观众被迷惑的眼根等因缘和合之后,凭空出现的事物,所以它没有实有的自性和本体。
中观宗以幻化为喻,说明一切万法依缘而起,没有自性。我们的房屋、身体、心理状态等等等等,一切万法没有一个不是依缘而起的,它本身没有自性,没有实实在在的主体。某种因缘具足了,某种因缘和合了,它就出现了,所以说是假立的,没有真实的自性。了知了一切都是依缘而起,都是幻化的,就不应该嗔恨这些如幻如化的事物,因为并没有一个操纵的主体可以被我们嗔恨。
前面所讲的任何内容都围绕同一个重点,就是没有自主。为什么要这样观察?因为如果认为有一个主体刻意发心伤害我们,我们容易产生嗔心;如果找不到一个主体,找不到一个负责的对象的话,我们就不太容易生嗔心。现在我们经过分析了知,一切的能嗔、所嗔,其实都是一种幻化的现象而已,并没有谁在幕后主宰、操纵这些东西,一切只不过是因缘和合之后自然而然地显现,本质上并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对境,也没有一个我们可以去实有嗔恨的对境。以此道理来息灭我们的嗔恨心。